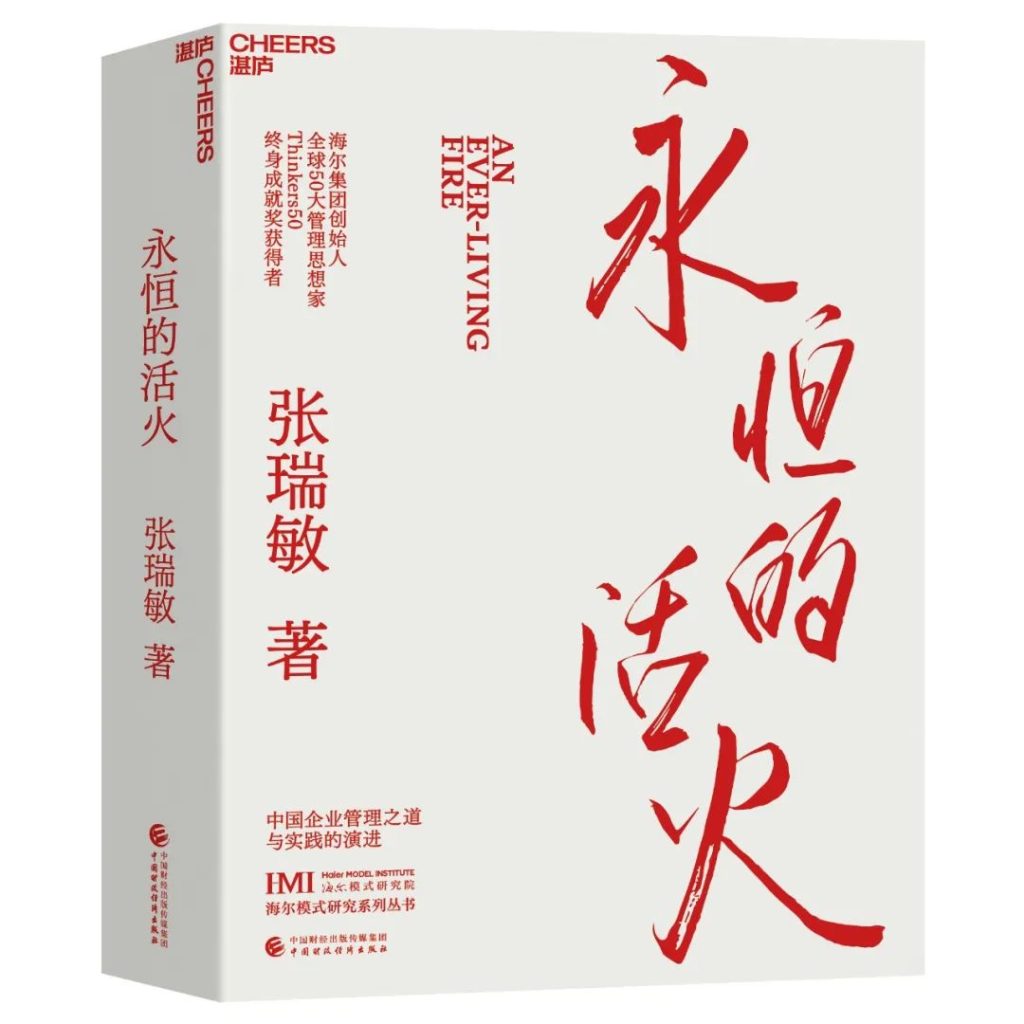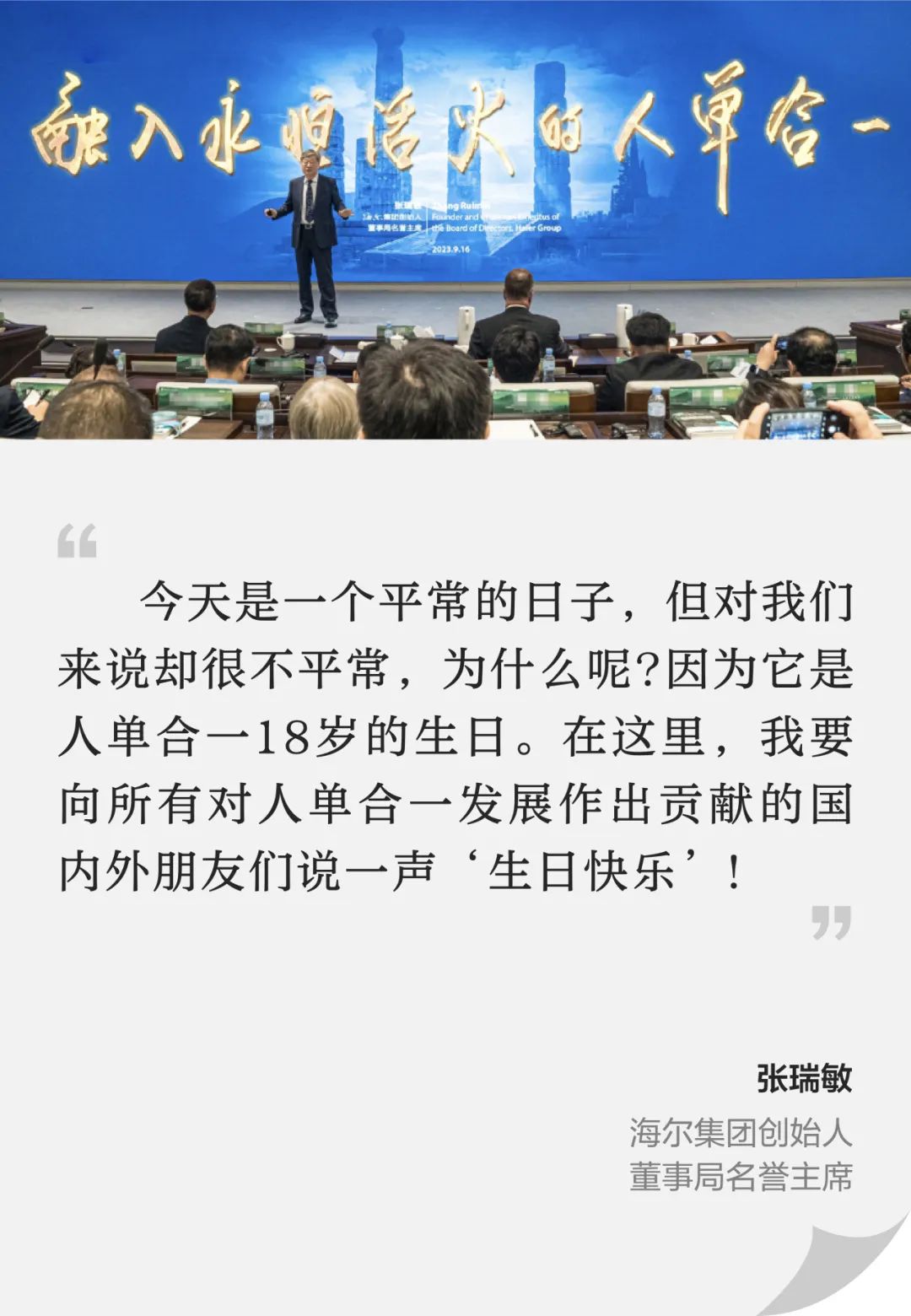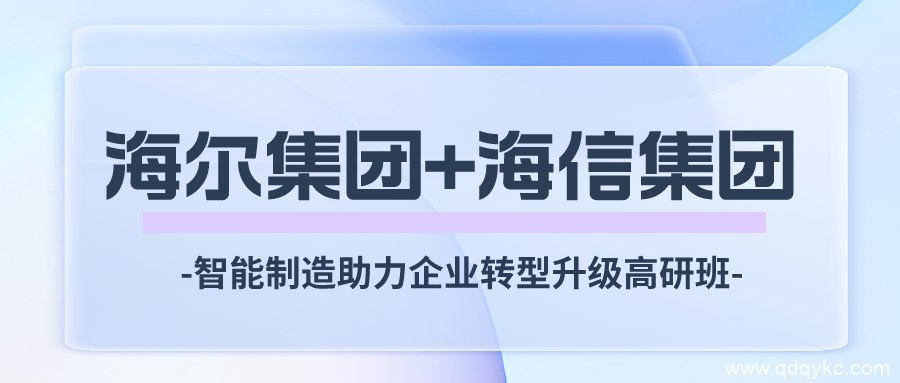4月22日下午,张瑞敏与《大爆炸式创新》作者拉里·唐斯(Larry Downes)进行了深入交流。
- 颠覆组织,应对“大爆炸式颠覆”
张瑞敏:你是我们的老师。你的《大爆炸式创新》《颠覆定律》,我们都反复地学过了,并在内部运用。而且,我还到处推荐《大爆炸式创新》,很多人读了都觉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昨天给我们的员工创客们上了非常好的一课。你到海尔来的这几天,看了很多,也交谈了很多,能不能再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需要怎么做?
拉里·唐斯: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发现海尔做的其实比我在书中所预言的更好。能够看到有人在现实中把这些理论运用得这么纯熟,我有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因为我可能不知道读者是谁,但我的书却可能会启发别人。
昨天,我非常有幸参加“创客咖啡”这样的活动,见到了非常多的青年创业者。他们非常有干劲,非常有活力。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干劲和活力只能在初创企业中出现,所以,我非常惊奇,像海尔这么大体量的公司,员工竟然这样有干劲,有活力,真是很少见,也让我感觉非常兴奋。昨天,我在“创客咖啡”给这些年轻创业者们提了一些建议:第一,希望这些创业公司可以像硅谷里的创业公司一样勇敢地去做;第二,不仅仅要跟用户交互,更要与用户合作;不仅仅是设计上的合作,而且要在整个生产过程,尤其在产品的信息收集、对信息的应用这些方面跟用户进一步合作。
张瑞敏:我们从您那儿得到启发且正在运用的,很重要的就是摩尔定律。我们要求大家一定要有指数科技,这就要求一定要整合市场和用户,要开放资源、整合全世界一流资源。为此,我们把考核变成两类:不仅要有产品销量、利润等传统指标,更重要的是用户资源。
拉里·唐斯:上周刚好是摩尔定律提出五十周年。大概戈登·摩尔(Gordon Moore)1965年提出“摩尔定律”时想到的是,这个定律可能在十年之中是有效的。没有想到五十年之后,这条准则仍然有效。而且,公司必须和消费者紧密合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我感觉,海尔也是这么在做的;您对企业进行的一系列相关的改革,就是按照这个方向在做。
(戈登·摩尔)
张瑞敏:您在书里面写得非常清楚,但我们做的时候却是非常难的。过去,特别是大企业习惯于研发是封闭的,但按指数科技的要求,要完全打开,一定要和全球资源结合起来,因为我要和用户结合在一起;根据用户需要来变革,关门研发不行。开门其实是很难很难的,我们做了很长时间。
拉里·唐斯:其实,并不只是您感到不易,我觉得对很多大企业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海尔比很多大企业做得好,因为海尔已经看到开放比关闭要好得多,而且也做出了一些非常显著的成果。我知道,我这么说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站在实施者的角度,真的是非常难。对大企业来说,这种关门研发可能还会持续一些时日,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应当将顾客和供应商一起拢合到设计环节上来,管理范式也需要相应地做出调整和改变,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更好。
张瑞敏:我们把研发开放之后,供应商、研发者都要进来,流程从串联变成了并联,也费了很多周折。你在《大爆炸式创新》里画的“鲨鱼鳍”有四个阶段:奇点、大爆炸、大挤压、熵。“要逃离熵,最后也是最大胆的一条策略是,找到一个仍处于早期阶段、市场上的试验还未成功的大爆炸式创新的市场,接下来重组企业,成为这个新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观点我非常欣赏,因为创新无止境;不找到下一个奇点,就不可能在市场上立足。我们现在想,是不是可以把整个组织划分成很多小的、可以自演进的自组织。自组织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开放的,可以引入更多好的资源而不是封闭式的;第二,正反馈循环,可以不断和成果结合起来。这可能可以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及早解决,而不是等到最后的熵阶段。
拉里·唐斯:非常赞同。在熵阶段才从市场上退出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在大挤压时就开始从市场中退出,我在书中也举了一些例子。当然也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在熵阶段仍做得很成功,但部分企业如果在熵阶段退出,前景就非常不乐观。
把企业拆分成很多小企业,其实就是想让这些小企业更加灵活地逃离“黑洞”。而且,这些小企业在奇点时就可以展开非常多的试验,大部分的试验可能是不成功的,然而,但凡有一两个成功就可以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张瑞敏:我们希望可以变成很多的创业团队,每一个团队都有一个“鲨鱼鳍”:有一些可能在奇点阶段,有的可能在大爆炸阶段,有的可能不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有很多业务处在大爆炸阶段,这个企业就会生生不息。
拉里·唐斯:今天上午,我跟轮值总裁梁海山先生进行了交流。他提到,对海尔来说,具有颠覆性同时也充满机会的地方就是物联网,因为物联网是把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相结合的一种网络技术。物联网在任何地方都是属于很早期的阶段,但是我觉得海尔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与之相关的产品开发、探索有好多。在今后,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技术方面的创新,尤其是大爆炸式创新的技术,希望看到海尔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引领。
-
科斯定理+摩尔定律=?
张瑞敏:你写道,打造顶级企业有十二条法则,很多都提到科斯和科斯提出的一些理论。
拉里·唐斯:其实,《释放杀手级应用》是《大爆炸式创新》的一个“前传”。我写了《释放杀手级应用》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感到在互联网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会在不同行业产生一些不同的影响,所以就写了《大爆炸式创新》作为一种补充。
(科斯)
科斯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我正好是他的研究助手。我非常崇拜他,而且也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科斯教授本人书面的著作很少,可能就发表过几篇学术论文,都是寥寥数语,提出问题也是寥寥数语。但是,他从来没在市场上有影响力,而且他的一些观点让经济学家感觉到非常震惊,因为科斯教授的好多理论都是极其颠覆性的。他曾经被拒绝加入学校的经济学部,而是到法学院教书,最终他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试图用经济学解释法律如何运作,并且在这两方面都有不俗的成就。虽然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谦逊、非常平静、温和的人,但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且,我从科斯教授那里学到一点,对我来说挺重要的,组织并不能够非常有效地适应市场的发展。当然,我通过对指数科技、摩尔定律的观察发现,技术(进步)可以使市场变得非常有效率。但是,与此同时,组织也会变得越来越小,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张瑞敏:我们刚开始变革时,受到社会上非常大的质疑,主要质疑就是把大企业分成很多小企业不符合“科斯定理”,因为按科斯定理所说,组织内交易成本一定要比外界低,这样才有竞争力;变成很多小企业,交易成本很高,因此不能够做好。
拉里·唐斯:其实,可以这样来分析他们所说的交易成本问题。海尔下面有很多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有自己的迭代技术,可视为平台,这么多平台实际上是可以将交易成本降低的,因为有足够的相关支持。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方面,有了这样一种架构,不仅仅可以在不同小微企业之间进行交流,而且由于这个平台本身是开放的,因此可以很好地跟供应商、顾客、分销商进行交流,这样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张瑞敏:科斯说,因为要经过很多程序,这么多流程就形成了市场摩擦力,从而使得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但是互联网来了之后,可以零距离,可以面对面,这些市场摩擦力就消失了。是不是本质上在这个地方?
拉里·唐斯:关于这件事情,我本人也请教过科斯。科斯教授本身并没有写过互联网方面相关的书籍,当我在推出《释放杀手级应用》这本书的时候,科斯教授当时读了一些章节,还给了我一些建议。因为现在跟传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前,技术首先是在公司内产生然后再推到市场上去;在互联网时代,指数科技事先在市场上产生,之后才会被引入到公司里并进行应用。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技术的改变是具有颠覆性的。
而且,科斯定律跟摩尔定律混合起来能发生一个积极的作用,比如说,电脑刚开始是政府、军方作为一种技术工具使用,也只有这些机构才能够使用它,当电脑的价格变得稍微便宜些的时候,像GE这样的大企业开始采用电脑;到了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更小一些公司开始使用电脑;随着摩尔定律起作用,1990年代,工人也可以使用台式机,而且逐渐有了手机,因为价格一直在下降。
张瑞敏:所以,虽然很多人质疑说我们的做法不符合科斯定理,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的:把很多中间管理层去掉,使组织彻底颠覆,越扁平可能市场的摩擦力会越小。
拉里·唐斯:我虽然不能代表科斯教授来说话,但从我自己对他的作品以及对他本人的理解,我认为您是真正理解了他的。而且,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并不是特别理解科斯教授的很多理论。在获得诺贝尔奖时,他这样说过,“在我生命的漫长岁月中,我认识过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我从未指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没有在高深的经济理论上有任何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只是促使把经济体制的特征纳入到我们的经济分析中。”
- 大企业为什么不“自我颠覆”?
张瑞敏:我在想,你可以再写一篇“大爆炸式组织创新”,因为如果原来的组织结构不颠覆,可能很难产生很大的创新。
拉里·唐斯:如果我要继续写这样一本书的话,很多研究可能就得仰仗海尔以及您的专业,因为我觉得海尔目前的结构变化甚至比海外很多企业做的都好。我承诺我会写这本书,也请您承诺您会继续进行这样的变革以供合作。这是非常必要的。
张瑞敏:在探索组织变革时,我也到美国、欧洲好多大企业去看过、交流过。比如,我跟IBM原来的总裁郭士纳谈海尔的变革时,他说非常好,他在任时也想做,但最终没有做,因为IBM几十万人,一旦做不好可能就全乱套了。
拉里·唐斯:资本市场本身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其实,我也跟很多CEO有过很多的交流;这些CEO会这么跟我说,华尔街是不会允许我这么做的,因为我需要关注下一个季度的业绩,再下一个季度的业绩,再再下一个季度的业绩。即使我看到在遥远的未来有这样一个光明的前景,但还是不得不止步。
张瑞敏:的确,IBM的人也说他们不敢做,就是因为华尔街不允许。但是,现在的问题,正如您在《大爆炸式创新》里面所说的,是“无章可循的战略、无可控制的成长、无可阻挡的发展”。既然预见到大爆炸创新无可阻挡,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柯达、摩托罗拉。大企业如果不能自我颠覆,不能爆炸式创新,可能就被大爆炸式创新所淹没了。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否则可能有很大一批传统企业要迅速被“挤压”掉。
拉里·唐斯:我感觉,柯达和摩托罗拉这些企业的衰退,是因为它们的管理者没有预见到颠覆是迫在眉睫的,相反他们可能是遵循克里斯滕森教授的理论,认为颠覆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柯达一直在说还没到、还没到,所以还固守着影像技术而没有立即采用新技术。根据大爆炸式创新理论,颠覆是立即发生,迅速或即刻(见效的),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应对时间了。所以,很多的管理者虽然看到了新时代的端倪,但是并没当成一种警示,也没有意识到可能是下一轮的颠覆式技术。
张瑞敏:可以说,他们已经在熵这阶段,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其中,或者已经意识到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拉里·唐斯:我认为应当是您说的第一种原因: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很多人不管是在心理上,还是情感上都很难接受被颠覆,比如柯达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所发明的技术最终走到了尽头。
张瑞敏:我感觉,做企业可能要经过很多次的“自杀重生”才能基业长青。但是,危险也在这个地方——有时候“自杀”,可能就活不过来了。
拉里·唐斯:美国心理分析医生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描写了病人死亡的过程——否定、非常愤怒、逐渐妥协、抑郁、接受(Denial, Anger, Bargaining,Depression, Acceptance)。其实,这个过程对于企业来说也是类似的,互联网颠覆了很多企业,那些被颠覆的企业也从否定到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不同的是,企业的重生其实要比个体的重生要简单一些。
-
观念转变与颠覆定律
张瑞敏:企业要(自我)颠覆,最大的问题可能在观念。很多年以来,泰勒的“科学管理”之后,企业就变成一种所有人听命于一个人的结构,现在要变成老子在《道德经》里面所说的“太上,不知有知”,最高明的领导是部下不知道你的存在,他们在领导者提供的平台上自由发展,自己去找到奇点。相对而言,这样可能企业重生的机会大一些。
拉里·唐斯:我觉得,海尔在做的方向是对的。每一位员工在海尔有自主权,可以直接分享一起研制产品的胜利,同时共担失败。这种财政刺激和驱动是一种有效的驱动方式。而且,他们不仅仅能够给企业创造效益,同时也能够为自己创造收益,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企业难以接受的。
张瑞敏:现在我们还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员工从原来“我来了之后完全听从指挥”到现在“自己指挥自己”,企业从原来“我要管理你”变成“我是一个创业平台”,不是“给你提供工作岗位”而是“给你提供创业机会”,反差非常大,内部也有很多人非常非常不适应。为什么我们的改革持续了这么多年?就是观念的改变其实非常困难。而且我到全世界去找,美国、欧洲都没有找到一个大企业做这种演变的模型。所以您的书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拿着这本书要求高级管理人员都要读,要么你就改变观念,要么你就被“炸死”。
拉里·唐斯:听到您这么说,我倍感荣幸;可以帮您的忙,我非常开心。技术能力的变化,其实在我的第一本书里就已经提到,但人类的变化却没有跟上,很多人不能够迎头赶上技术发展的速度。
听说您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也读了非常多的书。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托马斯·库恩的书。他提到,科学范式的变化,通常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被接受。为什么呢?就是要等到老一辈科学家退休之后。当第一轮互联网颠覆波浪向我们涌过来的时候,我与很多CEO交谈。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们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但是很抱歉,我们没法胜任这种改变。希望在我们退休之后,变化能够发生”。
张瑞敏:对,这就是你在书中所说的“颠覆定律”,法律、社会条件等跟不上科技的发展,有很大距离。企业也是这样,企业文化本身是双刃剑。过去,我们要求员工必须执行到位,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海尔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可能就在于我们的执行力非常强。有的时候是企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原来要求你必须往东,现在又要求你必须往西走。现在要让他们创业,不要听上级的,而要听用户的。从听上级的转变成听用户的,从完全执行上级命令到自己创业,是完全不同的。
拉里·唐斯: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失败,是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基因的,尤其是在一个颠覆性技术盛行的时代里。海尔“永远自以为非”的理念,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两天前,我去海尔文化展看了一下,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刻:海尔第一次获得质量大奖的时候,当时您没有去表彰,而是开了一场自我批评会,寻找自己的不足。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成功,起着很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瑞敏:在实践中,我们对颠覆定律的体会更深。企业的制度是按照原来的技术设计的,现在突然改变了,要马上跟上确实很难。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讲,变革要先从改变观念、改革企业文化开始。
拉里·唐斯:当然了。随着企业的发展,“舰艇”会越来越大,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快,一系列颠覆式创新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快。
我觉得,虽然海尔不会比颠覆性技术跑得快,因为没有人能最终跑得过摩尔定律,但是海尔只要快过同样在互联网浪潮里挣扎的企业就已经是很成功了。海尔目前也是这么去做的,这也是海尔非常成功的一点。
今天是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读书的企业家是如何读书的。
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老师和张瑞敏在交流了“慕课”、大企业病、管理中的人性、组织变革等问题后问道:
从张总刚才的谈话,感觉您的读书量是非常大的。您是怎么样找出时间来看书的?另外,我发现,您对大数据这些东西的接受度也相当强。
众所周知,俞老师是个读书人。他在某年北大开学典礼的演讲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
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大抵如此。
张瑞敏回答道:
我书读得挺多的,一年至少一百本。我看书和别人的方法不太一样。我会先把书很快地浏览一遍,想一下书里头到底哪几个部分可能对我们很有用,然后倒过来再看,就像牛吃草一样。这个观点对我们有用就仔细琢磨琢磨。有的书价值就不太大,而且书看多了之后就会发现,有一些书是类似的;有的则要仔细看,比如《大爆炸式创新》,这本书要仔细看,里面还有哲学。
4月22日下午,张瑞敏和《大爆炸式创新》作者拉里·唐斯进行了交流。交流结束后,唐斯参观了张瑞敏的办公室。拉里·唐斯是这么评价的:“您的办公室不是办公室,是图书馆!”
无独有偶,前几天,德国《经济周刊》的记者问张瑞敏“最喜欢读什么书”。
张瑞敏说:
首先是管理类的。管理类的书读了很多,我最推崇的、也读得最多的、所有能读到的都读了的,就是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书。
其次,关于互联网时代的书,比如在美国很有名的克里斯•安德森的《长尾理论》《免费》《创客》,凯文•凯利的《失控》,能够得到的都找来读。
当然,还有一种是读了之后,过一段时间会再拿来读的哲学类书籍,包括老子、孔子和孙子的书,还有其他诸子百家的。德国哲学家的书,我非常喜欢叔本华的。
 联系腾龙娱乐有限公司19987877778(客服)
联系腾龙娱乐有限公司19987877778(客服)